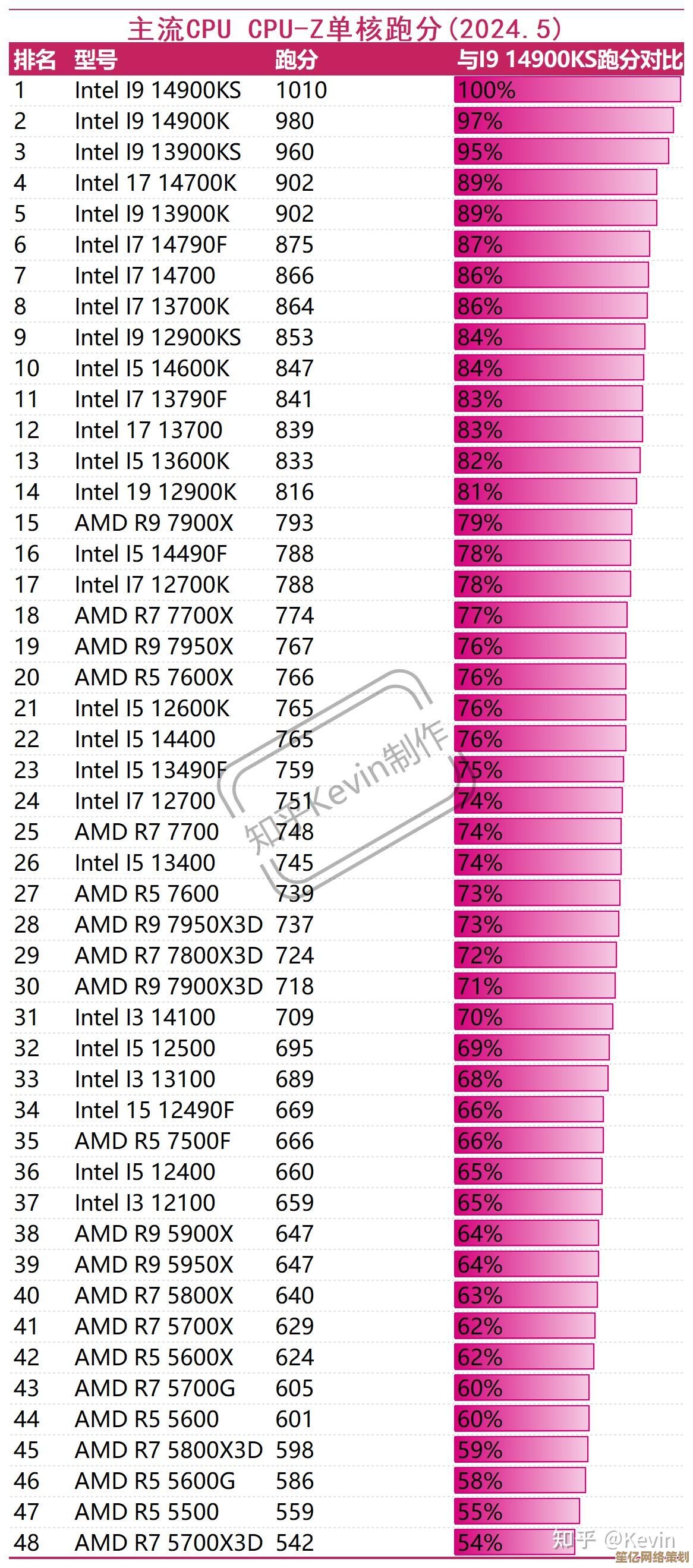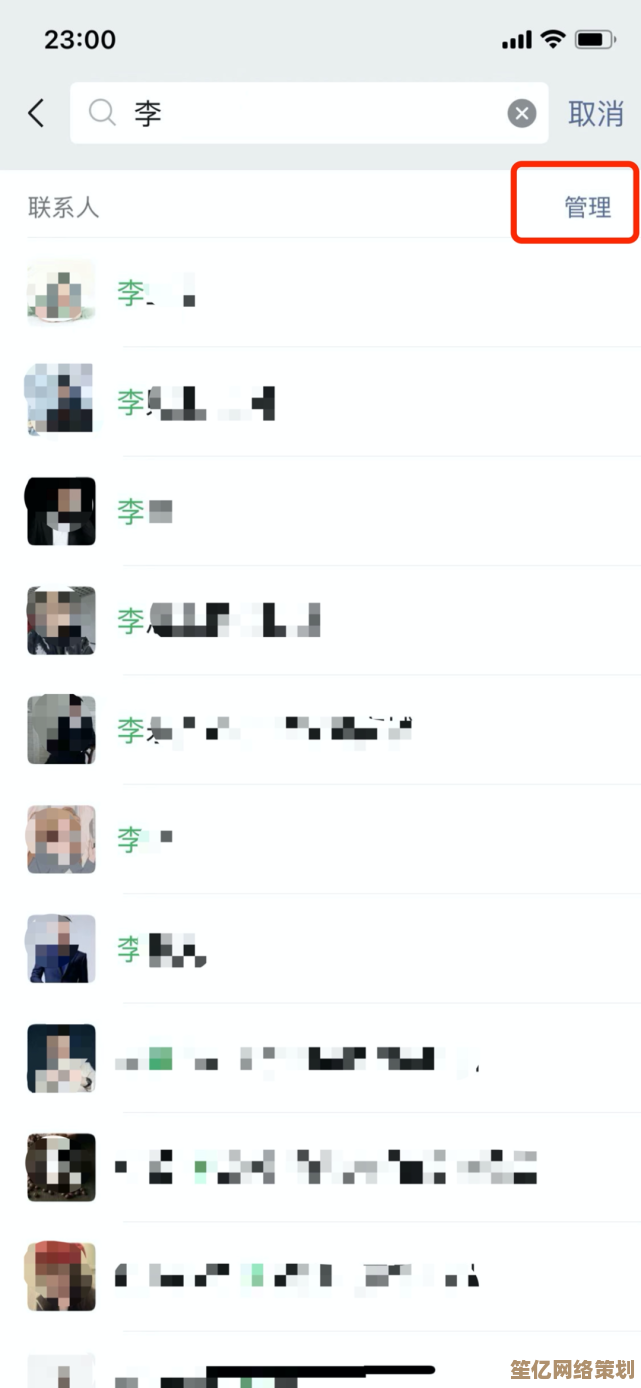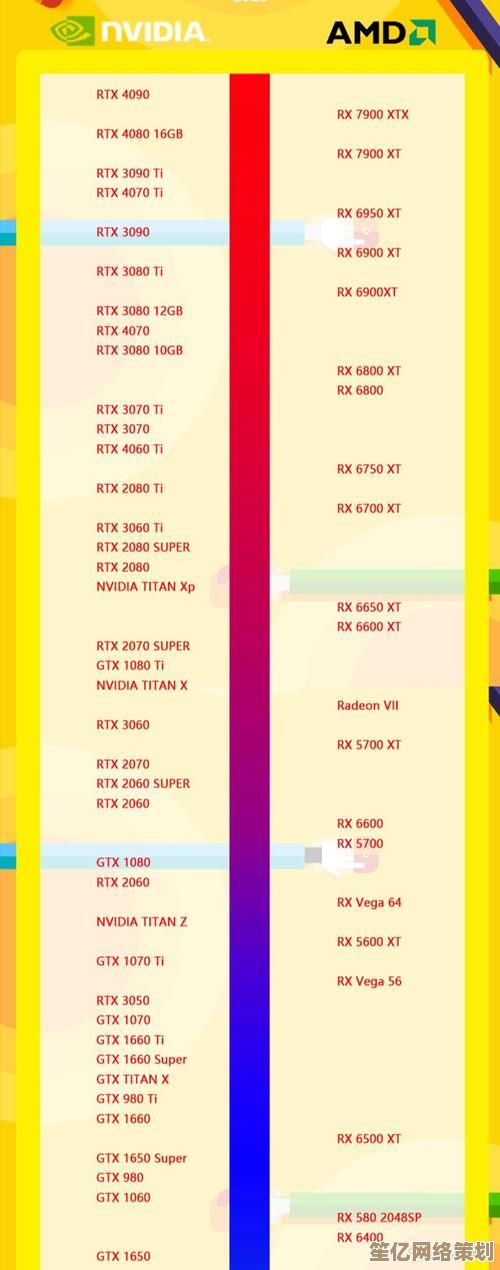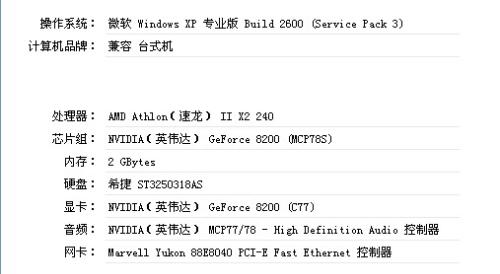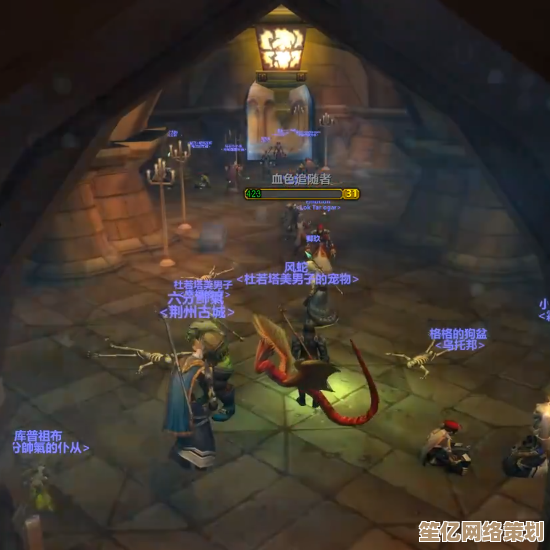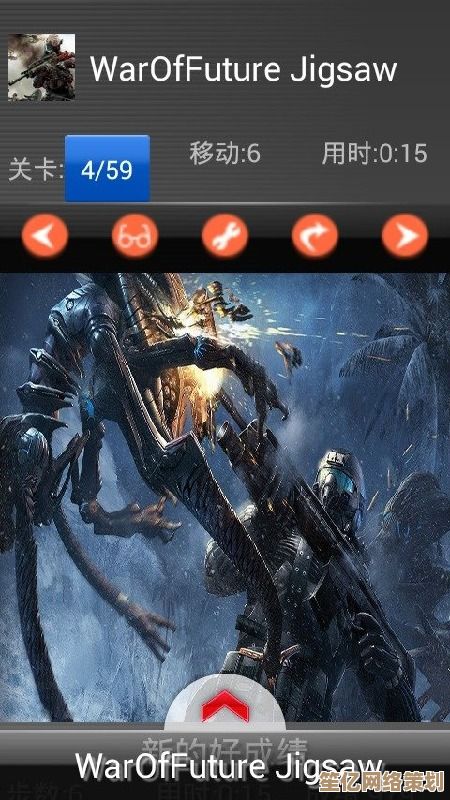FLAC无损音频体验:高品质音乐爱好者的完美音质选择
- 问答
- 2025-09-20 13:09:29
- 2
FLAC:当音乐不再是背景,而是入侵你灵魂的暴徒
我是在某个凌晨三点发现这个秘密的——当我把那首听了十二年的《加州旅馆》从MP3换成FLAC格式,老鹰乐队吉他手的手指在尼龙弦上滑动的颤音突然变成了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的耳膜,那种感觉就像有人突然掀开了蒙在音响上的三层棉被,而在此之前,我居然以为那团模糊的声响就是音乐的全部。
数字音乐的"皇帝新衣"
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Spotify上320kbps的音频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星空》,而苹果音乐的AAC格式充其量是幅印刷品,去年帮朋友调试他那套二十万的柏林之声系统时,这个玩黑胶十几年的老烧友盯着我手机里的FLAC文件,表情活像发现了妻子出轨——"这些零和一的组合怎么可能有模拟味?"
直到《波西米亚狂想曲》里那段歌剧段落响起,弗雷迪·墨丘利的齿音在"Galileo"这个词上炸开的瞬间,他默默把唱针抬了起来。
细节暴政
FLAC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会让所有录音瑕疵现出原形,某次用拜亚动力DT1990听某流量歌手的现场FLAC,背景里修音师手忙脚乱滑动音准线的声音清晰得像是坐在调音台上,这种赤裸感让人想起第一次在4K镜头里看清自己的毛孔——既恶心又上瘾。

但真正的魔法发生在古典乐,DSD64格式的《贝九》第四乐章,当定音鼓手在"Freude!"处那记失误的弱拍被揪出来时,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指挥家会当场砸烂谱架,这种级别的细节还原,让音乐从消费品变成了共犯。

存储空间的阴谋论
当然有人会说256GB手机装FLAC是行为艺术,但当我发现某张日本版《月之暗面》24bit/192kHz版本比CD大三十倍时,突然意识到这根本是唱片公司的阴谋——他们早该在九十年代就给我们FLAC,而不是用MP3驯化出两代人的塑料耳朵。
上周我把1983年东京演唱会的FLAC版灌进Walkman,大卫·吉尔摩在《Comfortably Numb》solo段落里那根断掉的琴弦,在左声道划出的金属哀鸣,让我在早高峰地铁上哭得像条被踢的狗,这种体验,Tidal的所谓母带级流媒体给不了。
现在我的硬盘里躺着1.4TB的FLAC,像一群随时准备暴动的听觉恐怖分子,它们教会我一件事:当你能听见歌手咽口水的声音时,音乐就不再是背景噪音,而成了刺向庸常生活的凶器。
本文由歧云亭于2025-09-20发表在笙亿网络策划,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waw.haoid.cn/wenda/4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