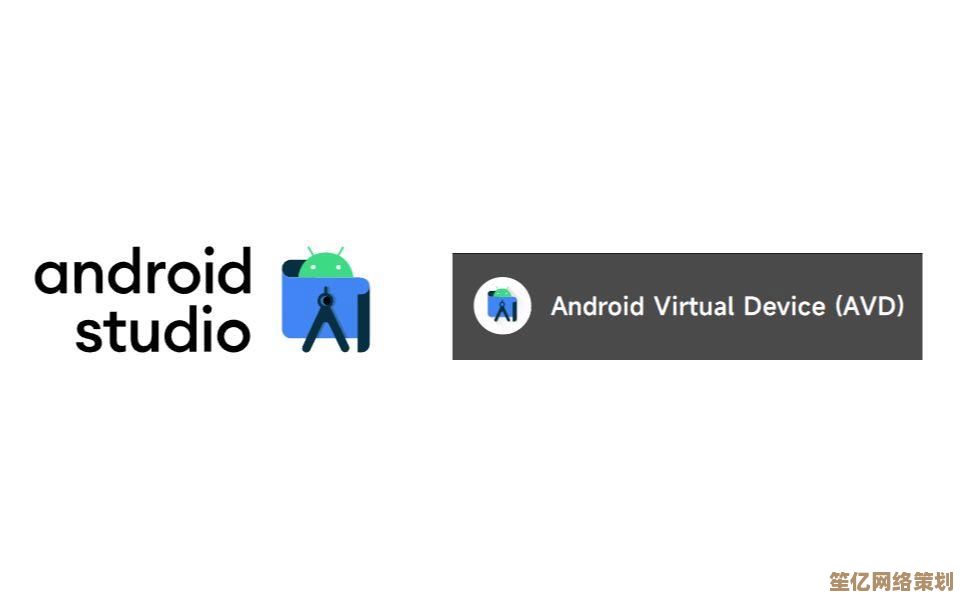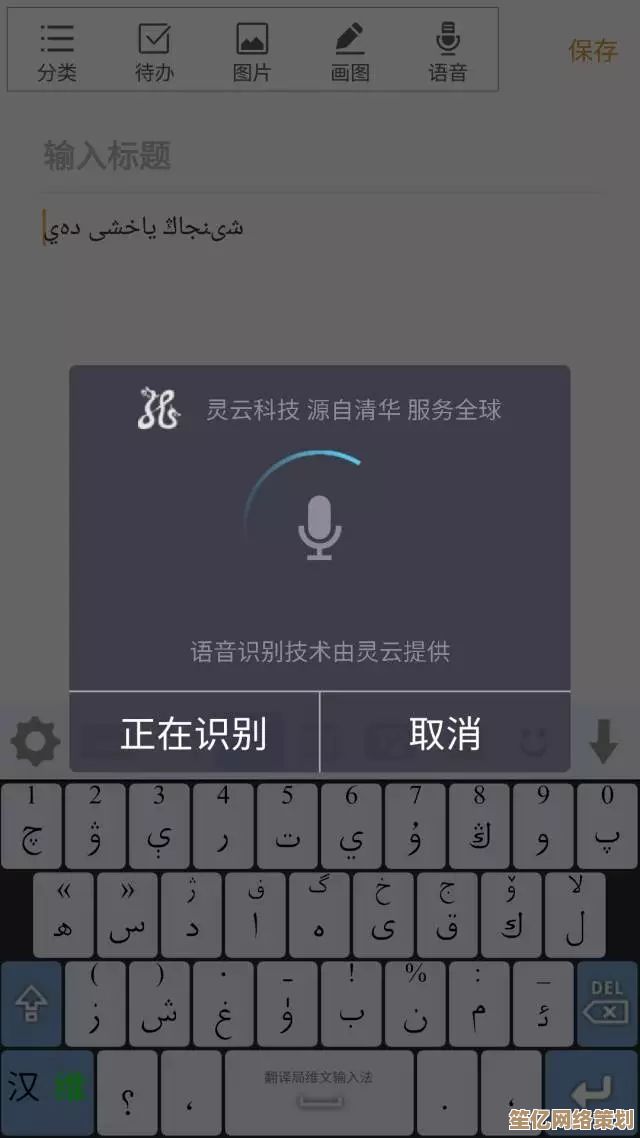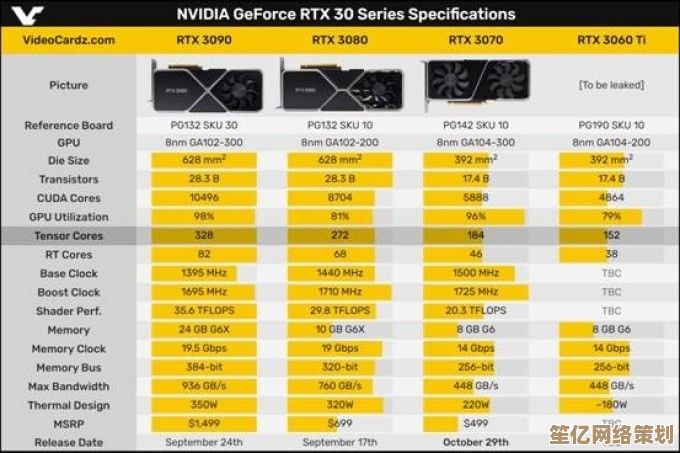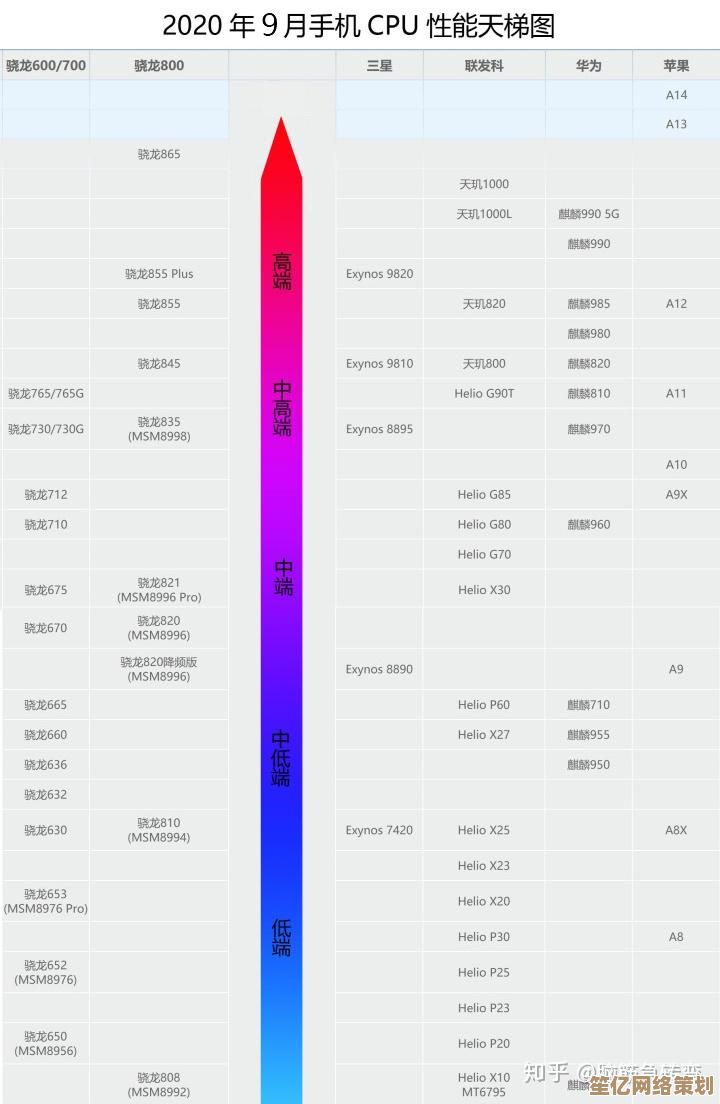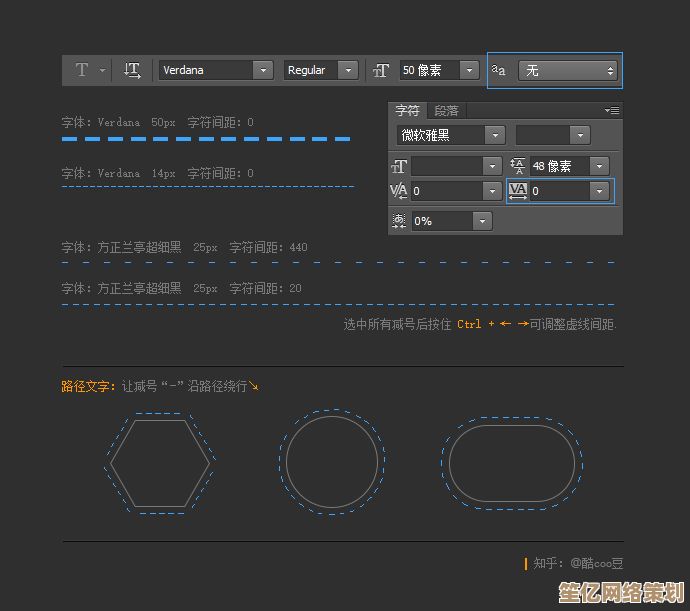时光镜头下的珍藏:老式相机天梯图的艺术怀旧与视觉叙事
- 问答
- 2025-10-03 20:00:33
- 1
📷 那天我在二手市场角落翻到一台海鸥DF-1,取景器里还卡着半张1987年的胶卷纸片,我突然想,这些老家伙们肚子里到底装着多少没讲完的故事啊?
有人说收藏老相机是“烧钱”,我倒觉得更像在时间河里捞漂流瓶,每台相机都不是冷冰冰的工业品——禄来双反的腰平取景器会逼你鞠躬般俯身,哈苏500CM的快门声像咬开一颗苹果,林好夫技术相机得用黑布蒙头操作,活像在给时光施法。🎞️
去年我经手过一台战前蔡司伊康,皮腔裂得像干涸的河床,本来想当摆件,却意外发现夹层里有张维也纳歌剧院的票根,我用医用胶带补了皮腔,装卷试拍时,那种带着漏光的成像效果,恍惚间真像摸到了1930年的衣角。
老相机天梯图从来不该是参数排名,而是叙事索引,玛米亚RB67和宾得67同样拍中画幅,但前者像扛着石磨修行,后者却像揣着板砖逛大街——重量相似,体验差出半个世纪,日本机械相机总把过片杆藏在右手拇指处,德国机却偏爱左侧拨片,这种设计差异里藏着民族性格的密码。
我总幻想给每台老相机建立“视觉族谱”,美能达X700的电子提示音是初代宅男的情书,尼康F3的钛帘快门藏着阿波罗计划的余温,哪怕是最普通的奥林巴斯OM-1,取景器里都住着1970年代东京的晨曦。
现在用数码相机扫街时,我常突然愣住——没有过片杆的阻尼感,没有倒片钮的吱呀声,拍完甚至不能把热乎的胶卷壳敲出来显摆,技术进步抹除了太多仪式感,就像电厨灶取代了柴火灶,饭更香了,但少了那缕撩人烟味。
上周带着海鸥去拍弄堂婚礼,新郎父亲凑过来说:“这机子我结婚时也用过”,他教我旋镜头筒的手势带着某种庄严,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是摄影师,倒像在传承什么巫术。✨
或许老相机的魔力就在于,它们用机械结构封印了人类对时间的贪恋,每次“咔嚓”都是与过去未来签订的三角契约,而我们都甘愿沉迷于这场永无止境的视觉乡愁。

本文由帖慧艳于2025-10-03发表在笙亿网络策划,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waw.haoid.cn/wenda/18277.html